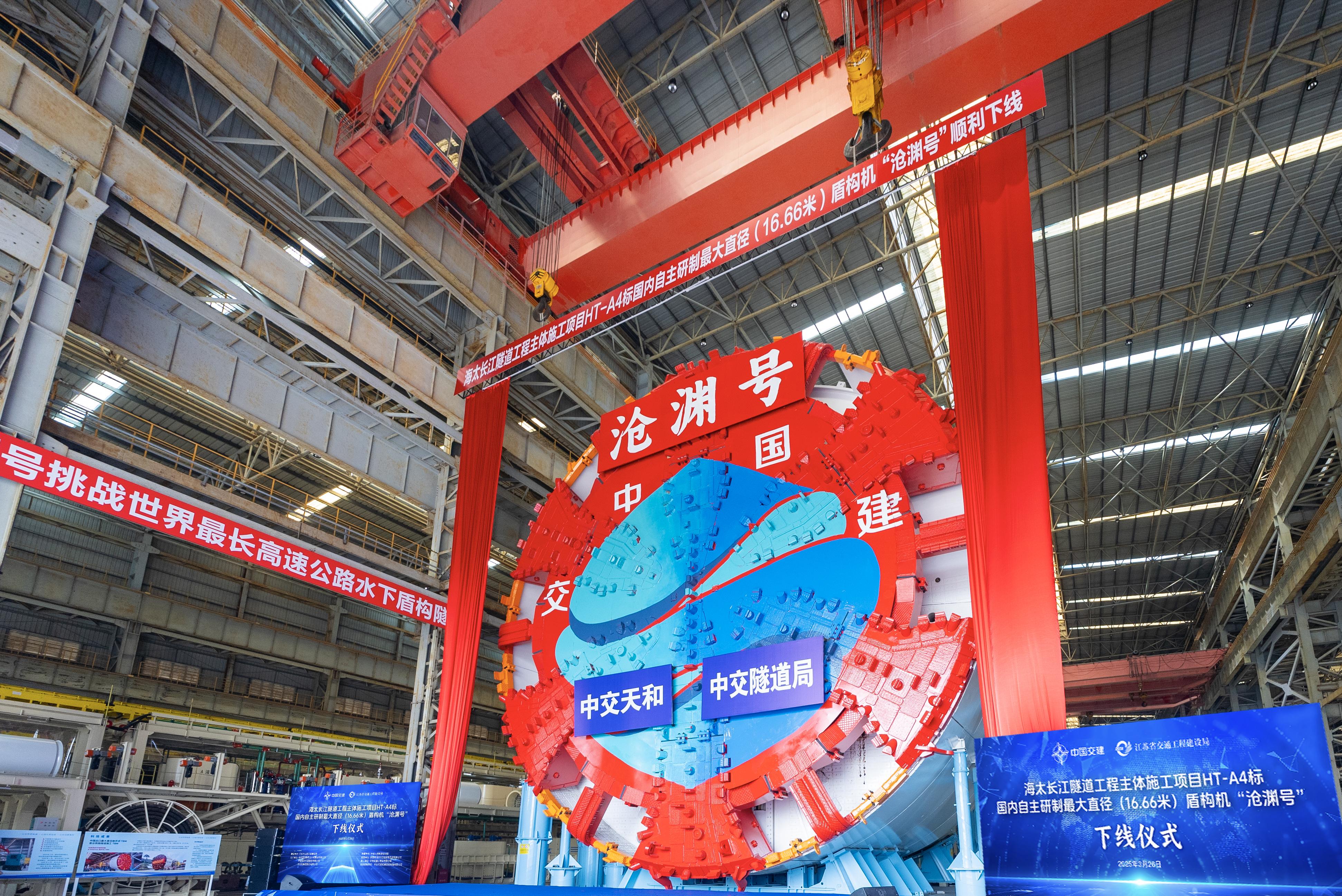菜園里,黃花菜開了,橙色的花如長長的金針。
黃花菜,古稱萱草,忘憂草,西晉的《博物志》:“萱草,食之令人好歡樂,忘憂思,故曰忘憂草。”世人皆知萱草可以忘憂。
黃花菜葉片狹長而光亮,似蘭草,花開狀如漏斗,微卷,花瓣肥厚,色澤金黃,采擷黃花菜,最好是在含苞時。
對于黃花菜,我再熟悉不過了,老家菜園里四周種下一蓬又一蓬,黃花菜似乎不用施肥澆水,依然生長得很好。初夏,黃花菜便生出一枝主干,上而長滿了大大小小的花骨朵。晨光微露,母親就踩著露水到菜園里,采摘那些似開未開含苞的黃花菜,母親容不得黃花菜開,因為開了花的黃花菜就只是花,而不是菜了。
記憶里,清晨的薄霧中,我喜歡牽著母親的衣角,踩著露水采摘一支支黃花菜的花骨朵,掐摘時聲音清脆,似有汁液四溢。嫩黃的花蕾,如長長的金針,家鄉人常叫它金針菜。綻開的花兒,端莊恬靜,有一種靜美。
萱草花生來就是為母親開的。天天有得開,日日有得采。母親清晨醒來,念及的是異鄉游子,但這時含露的萱草要采摘,忙碌間情感轉移,也就忘憂了。古時游子要遠行時,先在北堂種萱草,希望以此減輕母親的思念,忘憂。唐朝孟郊《游子詩》寫道:“萱草生堂階,游子行天涯;慈母倚堂門,不見萱草花。”
有一天,在《詩經》里讀到“焉得諼草,言樹之背。”朱熹注箋曰:諼草,令人忘憂;背,北堂也。萱草英文譯為“daylily”,意思是只開一天的百合花,因為單朵萱草,往往凌晨開放,日暮閉合,午夜萎謝,只有一天的美麗。讓人有點傷感,似轉瞬少年老,心底落滿霜。但也不必愴然,翌日清晨,依然有一兩朵再度綻開,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,如此,一直持續整個夏天。
黃花菜,一蓬葉一蓬花,看上去是那樣美好。那百合狀的萱草花是一朵接一朵地開著,在微風中搖曳著。
深秋,母親會托人捎來沉甸甸的一包黃花菜干,菜干為褐色,已失去往日的鮮潤,觸手干硬。而今,母親老了,失去年輕清秀的容顏,像那曬干的黃花,但那一雙凝望的目光,穿越山山水水,綿延著無盡的母愛。